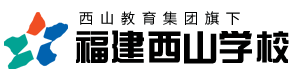我想,草籽枕头的青春,姨婆的青春和村庄的青春,大概是一起逝去的。
譬如当姨婆掉落第一颗牙齿,村里倒下第一栋年久失修的老屋;当无人问津的草籽枕头因姨婆的日夜摩挲而终于破裂,村里的人也像枕头里的菜籽一样哗哗流去,散落四方……
如果我们就把这叫做老去,那什么能被称为是青春。
在姨婆一口结实整齐的牙齿能干净利落地咬断草茎时,我想她是青春的;在她能每天早上四点半利落地爬起,与村庄里的女人们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去收草籽时,我想她是青春的;在我每年都换上了新草籽枕头散发出草木与大地干净而辛辣的气息时,我想它是青春的;在村庄还是鸡鸣狗吠,热闹非凡时,我想它是青春的……
站在姨婆的墓前,我撒下一把清香的草籽。肝癌夺走了她还不算太老的生命。可我知道,当村子里的人都千方百计地奔向城市,奔向羽绒枕头,姨婆就已不可能回到他的青春了。
回望身后,曾经长满稗草的湿润小径上尘土飞扬。宽阔的水泥路上,新建的小洋楼里住着的村人们,抑或是半个城里人们开着汽车,枕着羽绒枕头,过着他们不一样的青春。
心中莫名其妙产生一种释然。
没有人永远不会老去,可永远有人正在年轻。我曾经那么固执地想抓住的,不过是我心中姨婆的青春,村庄的青春。他们的青春逝去了,但仍可在我的心中不朽;而另一群人,亦在延续属于他们的,村庄新的青春。
再一次枕着姨婆留下的草籽枕头,耳边适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仿佛那些草木仍在枕头中拔节生长。经冬历春,枕中却封存一段岁月,永不老去。老旧的棉布轻抚我的脸,一如姨婆温暖的手。外面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新型收割机的轰鸣声,意外地不觉刺耳。
青春逝去,青春不朽。
指导老师:李春萍